會議回顧:ICLA 科幻的跨學科視角 ——文學與科學的沖突、融合與未來
2025年7月28日至8月1日,全球知名學術機構“國際比較文學學會”(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在韓國首爾召開了第24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2025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不僅正值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創立70周年紀念,同時還是聯合國所宣布的“國際量子科學與技術年”,比較文學研究的里程碑見證著當下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進行時不斷朝向未來推近。

第24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以“比較文學與技術”為大會主題,旨在探索科學技術對全球文學態勢的建構與重塑、審視文學表達與技術革新之間不斷發展的關系。而作為世界文學的科幻文學不僅映射時代科學技術的整體樣貌,而且以遠見卓識的驚人想象推演著技術的未來發展,在此次大會中無疑成為了極具討論價值的專題。第24屆ICLA大會的50號分論壇“科幻的跨學科視角:文學與科學的沖突、融合與未來( Literature and Science: Conflict, Integration and Possible Future in Science Fiction)”集中討論了科幻研究相關問題,吸引了國內外眾多學者參與,他們視角多樣的發言展現了科幻研究領域的最新動向與成果。
專題一
第一場會議發言涵蓋了數字世界背景下生命主體與存在形式的再思考以及文學與科學的演變邏輯等話題。
此次分論壇發起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王一平教授討論了賽博朋克科幻小說中出現的新型公共領域與存在方式,數字世界以包容性和公共無障礙性,從技術的角度重塑了公共空間概念,其中的生命呈現出三種主要形態,即人類的數字孿生體(the digital replica or "digital twin" of human beings)、“人類+”的有機與無機混合體( the “human+” hybrid that combines organic and inorganic matter),以及獨立于人類存在的數字實體(digital entities that exist independently within cyberspace)。王一平認為這些新的生命形態,挑戰了傳統的“有機生命沙文主義”(organic life chauvinism),引發了關于生命與死亡邊界的探索,尤其是數字意識延續與數字化復生的可能性問題,其意義不在于虛幻的永生,而在于重塑生命觀念、改變存在范式、并為新的存在形態構建整體性的本體論框架。
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何敏教授聚焦于科學與文學之間的動態互動,探討量子理論(Quantum Theory)與文學想象如何在概念和敘事層面上實現雙向流動。從科學到文學,量子理論在文學中獲得了“概念滲透”(conceptual penetration),為小說與詩學提供了新的敘事維度與審美可能。與此同時,從文學到科學,量子小說(quantum fiction)通過隱喻和虛構激發了科學思維的“反向賦能”(reverse empowerment),推動了科學家以不同方式重審理論框架與未來圖景。何敏教授認為科學想象成為重要媒介,承載并融合兩種認知模式,使文學與科學形成互嵌的關系,兩者的協同不僅重塑了現實的理解方式,也為建構科幻小說敘事提供了新的路徑,推動我們重新思考“現實”的邊界和意義。
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呂廣釗副教授以格雷格·伊根(Greg Egan)的《置換之城》(Permutation City)為例,深入探討了數字復生的物質性基礎及其對后人類主義、數字主體性與計算形而上學(computational metaphysics)的啟示。他指出,格雷格·伊根通過“塵埃理論”(Dust Theory)揭示了數字生命并非單純的意識延續,而是在算法決定性與隨機性之間生成的“數字換生靈”(digital changelings),他們具備自主的主體性,并通過算法與物質生成的糾纏來完成構建。與傳統將數字意識視為人類工具或威脅的敘事不同,這種設想凸顯了數字存在的物質糾纏與能動性,重塑了主體性、物質性與本體論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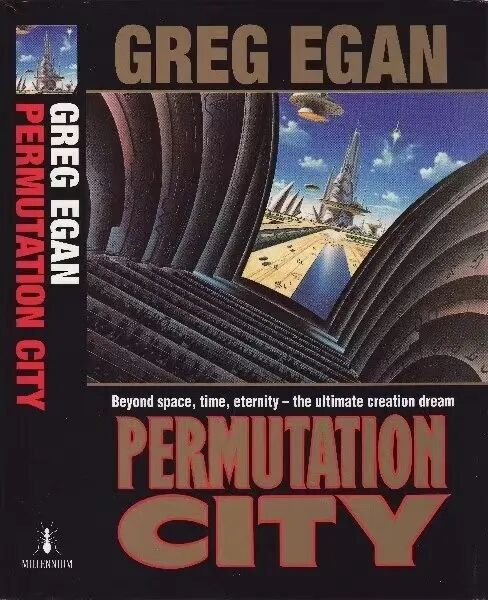
海南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曹牧原通過剖析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克拉拉與太陽》(Klara and the Sun),探討了后人類生存處境與神話敘事的結合。曹牧原認為,人工智能克拉拉以“太陽”信仰拯救基因編輯技術受害者喬西的情節,被賦予了奇跡般的神圣意味,借助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的哲學人類學理論,她指出未來社會中技術的極端理性加劇了現代人的生存焦慮,而人與自然,即人與神圣之間的疏離,使“顯圣”(Hierophany)只能依靠AI實現,并強調在數智洪流中“愛”(LOVE)始終是維系人類主體性的錨點,神圣與世俗的辯證共存構成了后人類生存經驗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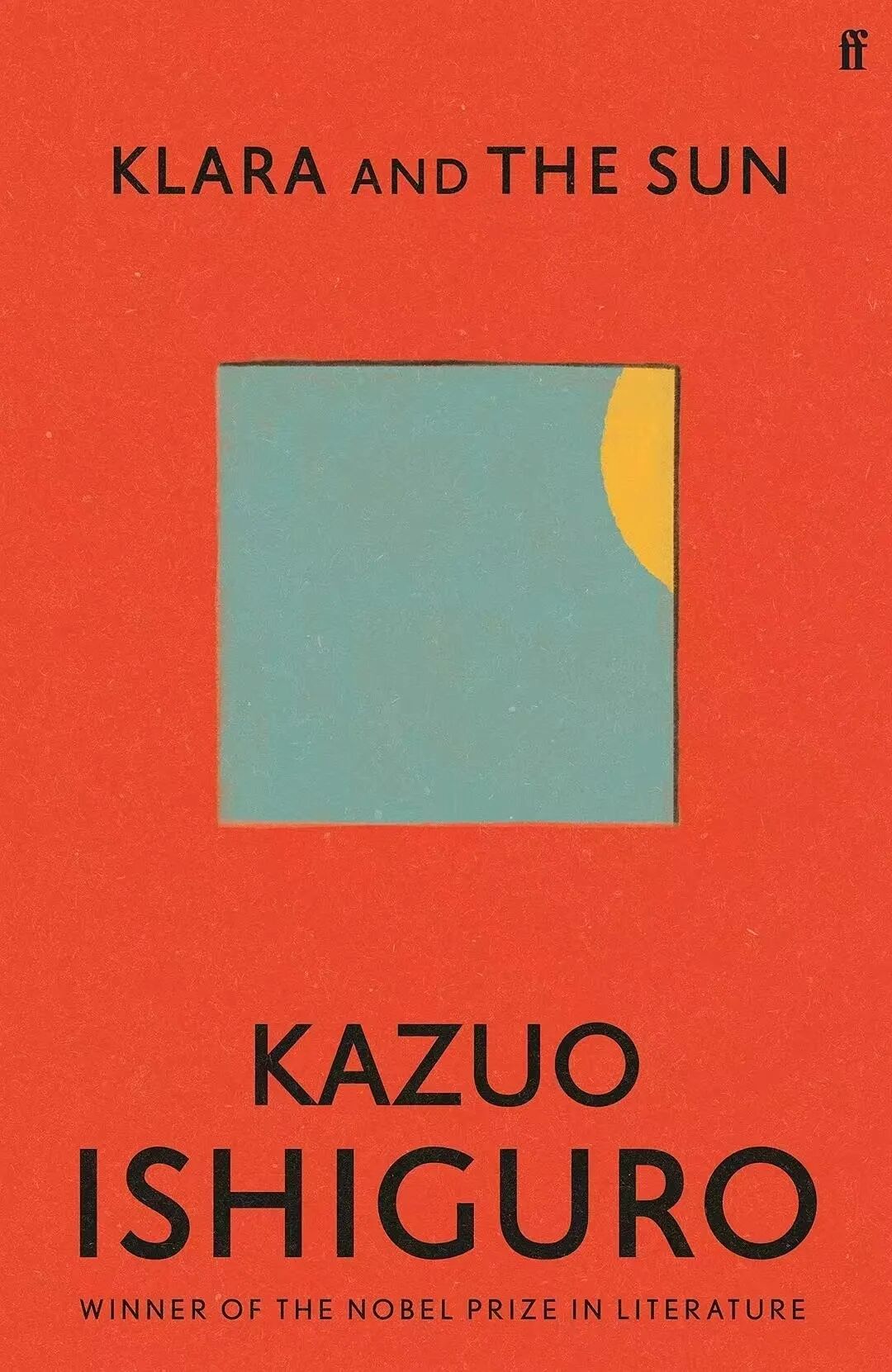
北京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蘇明明以當代人工智能科幻敘事為研究對象,討論了身心二元悖論與主體性建構內在邏輯的延續和突破。她通過對《她》(Her)與《克拉拉與太陽》的梳理分析,揭示出當代人工智能科幻敘事中的主體性模式,即主體通過與他者的互動構造“另我”(alter-ego),以滿足自我需求與欲望。這既反映現實社會的交往困境,同時表明對于存在本質的永不止息的追問。最后,蘇明明將科幻文本置于信息時代語境下,指出虛擬文化和消費主義生產邏輯雖導致了主體性異化,但人類自身仍具有能動性,告誡人們需警惕消費主義推動的擴張性主體模式,探索新的本體論生成邏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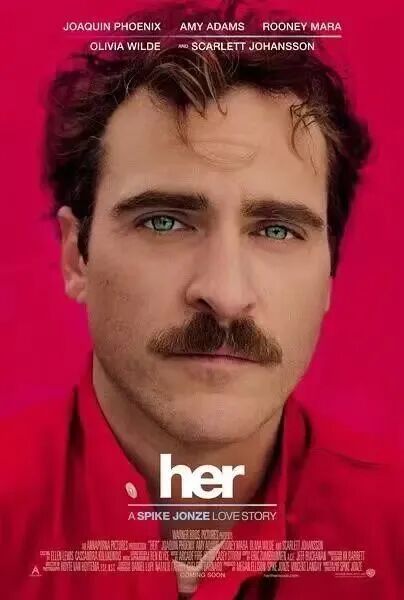
專題二
第二場會議發言中,多位學者在后人類、加速主義與生態危機的語境下,對科幻敘事中的技術、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進行探索。
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江玉琴教授探討了中國當代賽博格敘事的三個獨特特征,首先她認為中國賽博格敘事通過高科技反英雄敘事,表達中國科幻作家對人機沖突及未來社會的憂慮,其次中國賽博格敘事擅長借助中國古代思想中的“夢”(dream)之意象探索人機關系與人性本質,再者則是將賽博格作為應對人類異化的文化實踐,置于中國歷史和文化語境中,重新思考古與今、傳統與現代、人類與非人之間的關系,以追求新的平衡與穩定的未來。
德國吉森大學的西蒙娜·巴托洛塔(Simona Bartolotta)重新審視了科幻研究中“科學”的地位問題,批評當下學界過度強調混雜性,而弱化了科學理性在科幻中的核心作用。巴托洛塔認為,不加批判地接受將科幻視為“無本質”(has no essence)的概念,并不利于厘清其科幻史及其文學批評的意義,反而造成了神秘化與模糊化。這種傾向源自將科學同社會政治剝削進行簡單捆綁的謬誤,因為科學理性本身可能成為解放力量、抵抗“地方”(local) 和“傳統”(traditional)的壓迫。若模糊科幻中的“科學”與神話、民俗、超自然等世界觀和本體論之間的界限,也會抹去科幻的歷史與認知特性。她主張保持科學的科學理性內核,將更廣泛的異質本體論納入“推想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范疇。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博士研究生徐書悅探討了阿根廷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亞(Ricardo Piglia)的《缺席的城市》(The Absent City),她認為小說通過女性賽博格“馬賽多尼奧機器”(the Macedonio machine)展現了一則技術寓言,皮格利亞以阿根廷軍政府獨裁時期為背景,借植入亡妻意識的機械裝置,探討生命延續與人工生命的邊界,批判父權制資本主義、軍國主義以及冷戰背景下的科技發展邏輯。賽博格形象既是技術的,也是隱喻的,失去身體感知的女性賽博格陷入身份與主體性的危機,模糊了人與機器的邊界。《缺席的城市》揭示了現代人在科技快速發展中的焦慮,反思人工生命與復活死者的技術追求所潛藏的危險。
四川大學博士研究生左茂江以丹尼爾·凱斯(Daniel Keyes)的《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Flowers for Algernon)為研究對象,分析其中的“懷舊-加速-平衡”(nostalgia-acceleration-equilibrium)的敘事結構、情感互動以及對技術倫理的反思。他認為小說通過主人公查理因智力提升而經歷的成長和墮落,揭示出科技時代“加速”引發的生存焦慮和倫理危機,而“懷舊”象征著對加速的直覺抵抗,在加速體現的技術理性對情感和生活完整性的破壞之下,“平衡”則被設想為最終的出路,作品不僅反思技術進步造成的早熟、衰老和主體困境,也激發讀者對技術加速與生命意義的當下思考。
四川大學碩士研究生羅浩然以保羅·巴奇加盧皮(Paolo Bacigalupi)的作品為例,探討如何通過“食物危機”書寫展開生態批評,他認為巴奇加盧皮提出了兩條路徑,即“改造自然”(Transforming Nature)與創造新人(Creating Posthuman),前者通過基因工程、水利設施等技術手段試圖提升環境生產力,但實際上加劇了人與自然的對立,加深了資本主義對資源的壟斷與剝削,后者通過創造新人類以能夠適應極端環境,看似提供了未來生存的可能,但實際上是將生態責任轉嫁給了后人類,掩蓋了人類當下應承擔的責任。兩種路徑實際上都是人類中心主義和技術理性主義的延續,都強調了“適應”(Adaptation)而忽略了“Restoration”,反映人類面對生態災難時對補救行動缺乏信心,他提倡科幻文學的生態敘事不應僅停留于適應自然的技術幻象,而應轉向修復生態、建立人類與地球并存的生態共同體。
專題三
第三場會議多位發言人針對科幻語境下的技術、神話與文化敘事,對人機關系、倫理思想以及人類存在之邊界等話題展開討論。
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呂超教授以中國哲學家趙汀陽的本體論為基礎,探討科幻文學中人與機器人的倫理問題,首先梳理了“機器人”(Robot)概念的演變,并將其界定為通過機械手段制造的“人造人”(artificial man),科幻敘事中的機器人可分為無自我意識的圖靈機與具備自我意識的超圖靈機,隨后總結出四種倫理范式:神學主義、人類中心主義、非人類中心主義和后人類主義,進而探討人類與新“神”、新“物”、新“人”以及新“自我”的倫理關系。
西北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郭昕老師通過比較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和科爾森·懷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直覺主義者》(The Intuitionist)兩部作品,探討了“完美機器”(the perfect machine)的概念以及人機關系。她認為兩部作品雖然背景不同,但都共同質疑了“完美機器”的可能性,指出其失敗的根源不在于機器本身的缺陷,而在于人類制造過程中所投射出的階級、性別和種族上的偏見,結合笛卡爾身心二元論觀點,將機器視為人類的產物,其本質上是人性的鏡像而非獨立的存在,若人性與社會關系得不到改善,人機關系的理想未來便無從實現,“完美機器”設想也注定破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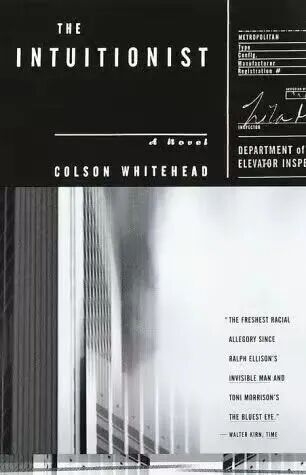
四川大學博士研究生王子彥深入解讀了丹·西蒙斯(Dan Simmons)的新太空歌劇(New Space Opera)代表作《海伯利安》(Hyperion),指出其通過神話與荒誕的書寫,展現科技與情感、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張力,小說借用希臘神話、浪漫主義與荒誕主義等精神傳統,創造出兼具機械與神性的“伯勞”(the Shrike)形象,體現了后現代神話敘事。她認為西蒙斯的故事揭示當人類在理性世界無法消解未知時,或轉向對神話與荒誕的訴求,這不僅是對理性主義的補充和抵抗,也是人類在科技主導的未來中尋求精神慰藉的方式。
四川大學博士研究生姜佑怡以“科幻人類學”(Science Fiction Anthropology)為視角,分析了青海冷湖火星小鎮(Lenghu Mars Town)案例,探討其如何通過科幻敘事與現實建構展開互動。冷湖依托于戈壁荒漠地貌、石油工業遺址和優質天文觀測環境,打造出具有“中國夢核”(Chinese dreamcore)審美的火星想象空間,小鎮通過火星主題文旅開發、設立“冷湖科幻文學獎”(the Lenghu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Award),推動科幻創作與產業發展。姜佑怡認為冷湖的科幻實踐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以地貌和遺址為資源,提供沉浸式火星體驗,二是依靠文學獎推動地方敘事,作為人類自我反思的“虛構民族志”(fictional ethnography),三是將科幻與科技、科普、產業相結合,利用虛構敘事反哺現實發展建設。

專題四
第四場發言涵蓋跨學科、跨文化研究以及對于科幻歷史與未來想象的考察。
西安工業大學文學院石燕老師探討了H. G. 威爾斯《時間機器》首個中文譯本《八十萬年后之世界》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與改寫,該譯本不僅受到晚清思想潮流的影響,承載著知識分子對未來社會的烏托邦想象,也融入了中國傳統游記的敘事方式,成為在民族危機背景之下的自我聊慰。這種“創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改變了援助的內涵與目的,凸顯出強烈的中國文化身份,譯介過程既延續了線性進步的觀念,又暗含對于進化論的質疑,折射出近代中國人在民族未來構想上的矛盾和猶疑。
斯洛伐克科學院約翰尼斯·卡明斯基(Johannes Kaminski)探討了科幻文學與未來展望(Future Foresight)之間的對話關系,他認為近年來科幻創作重新被視為一種探索復雜未來的方式,例如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MIT Press)出版的“十二個明天”系列(The Twelve Tomorrows-series),以及陳楸帆與李開復合作的《AI未來進行式》(AI 2041: Ten Visions for Our Future),都強調了科幻在提升公眾對科技與社會問題的認知與應對當中起到的作用,然而這類實踐往往將科幻降格為單純的教育工具或傳播手段,忽略了作為其核心的文學世界建構能力,事實上相關研究中的“情景思維”(scenario thinking)本身便源于假設事件鏈條、分析潛在風險與后果的敘事邏輯,其方法與文學批評中的“可能世界敘事語法”(the“narrative grammar”of possible worlds)存在巨大的對話與互補的空間,文學研究關注視角和規范原則,而風險評估則側重應對和緩解,它們在通過敘事探索未來不確定性方面具有深層次聯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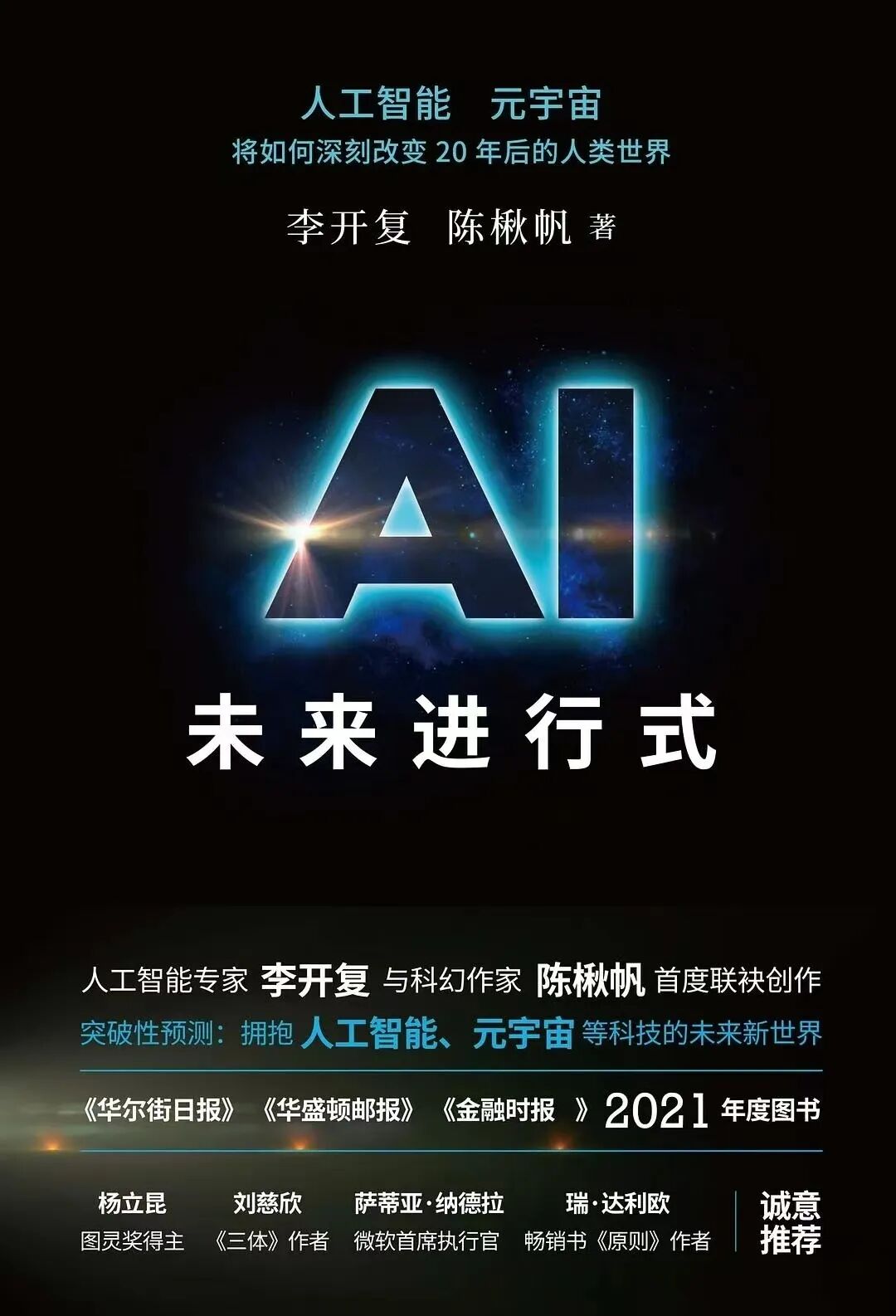
四川大學博士研究生譚榮珊從體認語言學(Embodied Cognitive Linguistics)視角,研究科幻小說中人類與人工智能之間的對話機制,通過整合體認語言學、概念混合理論(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以及隱喻-轉喻理論(Metaphor-Metonymy Theory),構建“現實-認知-語言”(reality-cognition-language)三元模型,再以《克拉拉與太陽》和《神經漫游者》(Neuromancer)中的人機對話為語料,采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分析AI如何借助隱喻、模糊指稱(vague reference)等策略突破人類中心主義,重構人機互動中的權力關系,她指出“離身語言互動”(disembodied linguistic interaction)對傳統語言認知模型提出挑戰,認為需要提出一種基于語言學的方法論以理解科幻敘事中的人機對話,為人機交互中的權力分配提供認知視角。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本科生岑嘉熙探討了在17世紀早期歐洲月球科幻作品中科學與神學間的互動如何推動理性探索與現代性萌芽,弗朗西斯·戈德溫(Francis Godwin)在《月中人》(The Man in the Moone)中描繪了應該英國文學史上首個登月故事,展現了一個道德完美的烏托邦社會,而另一位科幻先驅西哈諾·德·貝熱拉克(Cyrano de Bergerac)在《月亮諸國與帝國的滑稽史》(Histoire comique des Etats et Empires de la Lune)中則以諷刺的形式構建了一個顛倒的、無神的世界,岑嘉熙認為兩位均借助新興宇宙知識展開想象,分別體現了當時的兩種哲學路徑,一是經驗主義與技術驅動的理性道路,二是唯物主義與相對主義的懷疑道路。
整體上看,“兩種文化”的相互介入在當下已然成為一個事實。本次會議在多個維度上呈現出強有力的突破性。我們既能看到借由傳統學術進路對科幻文本的深度解讀,又有多種全新的研究范式被應用于科幻文化和實踐的探索。這些不同的理論立場和方法,指向的不止是文本之內的虛構世界,也充分折射出營造出文本及其評價體系的外部世界正在發生劇烈變化。而對于變化中的現實,我們無疑需要更多探索路徑、解釋方法和實踐方向,以此來促使學術增長和文化實踐共同走向歷史和未來的深處。
(整理者 羅浩然,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科幻文學、當代英美文學。)


